
“音乐、绘画、诗歌、戏剧,从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叠加与组合的艺术。只要时间足够,一群猴子在打字机上胡乱敲打,也能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
——引言
“我要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像一片会移动的罂粟花田,像一瓶吃不完的止痛药,像忠实的女奴,服侍欲壑难填的老饕主人。”
——吻瘾者
“他的亲吻温柔耐心,舌尖不漏过任何一个角落,像是在琢磨一段不好懂的文字。他给出的性爱则像一次漫长的朗诵,每个单词,每个段落,细致地咀嚼、吞吃,让它们融合到自己的声音和心里。”
——猜书人
“纪念物的意义就在于此:一种物化,或者说,一个寄存柜、一根系泊用的桩。比起失掉和死亡,人最恐惧的是一切竟会没有痕迹,宛如一场徒劳的、无意义的噩梦。”
——梦城
“所有作者都必须具有忍受羞辱和嘲讽的能力,我们把文稿送到世界上,就等于把脸伸到别人面前,等待掌掴。”
——盗贼合作者
“海滩是海向人世张开的手臂,是允准人们尽情凝视她打开的衣领之间的那一块肌肤。”
——海滩鉴赏家
“满心欢喜地走进生活的玫瑰丛,却被意料之外的花刺扎疼了。”
——魔术师的女儿
“世间母亲与子女的感情,源于怀胎时的脉搏相通,分娩时的切肤之苦,父亲们对子女的感情没那么自然。父爱大多始于惶惑:眼前是出于逻辑和伦理,不得不耐心应付的一个陌生来客(甚至像是个陌生物种),其贪婪自私、无法交流很容易惹他们厌烦、恼火。得等这团血肉面目清晰起来,有些模样,有些谈吐,他才能找到与之相处的乐趣,一日比一日惊喜地辨认出旧时的自己。这时父爱才算成形。”
——魔术师的女儿
“可这种背叛和逃脱又多么甜美。十九年的旧生活立刻显得陈腐无味,像是亟待褪去的蛇皮,它处处开绽,已经包裹不住注定要饱胀的欲求。”
——魔术师的女儿
“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生命的产生获得主动权。海德格尔说,唯一能把握生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
——里瑟先生的故事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儿女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
——H的故事
“所有活着的人,也只是闭着嘴,关上心扉,心中带着死念,涉泥淖,穿丛莽,不断往前走。”
——里瑟先生的故事
“对我来说,写完的小说就是前男友。希望他过得好,受欢迎,但不会主动联络。这里的小说五年间我没重读过。这次为了再版,打开旧文稿逐字逐句校订的过程,就像被迫跟五年不见的前男友见面,坐下来聊了次漫长的天。”
——后记
书中的故事,并没有那么惊艳,但也不俗套,我比较喜欢《陶丈夫》这个故事。
接下来是一段废话:知道张天翼(黑糖匣出版的时候还是以纳兰妙殊著)完全是个偶然,因为高中时候没什么消遣的东西,就只有聊聊天读读书,《黑糖匣》完全是我偶然的情况下,随手在舍友(绰号熊猫)床上抓来的。初读有些不适应,文字风格与我当时读的书截然不同(高中的我喜欢读余华的书,还有很多翻译味儿很重的国外小说),时隔三年已经不记得书里的内容,后来无意中在豆瓣看到了这个条目,才知道原作者叫张天翼,在豆瓣也有号,而且《黑糖匣》也添加了一个故事再版为《扑火》,就又重新读了一遍,第二次阅读就显得比较适应纳兰的文字风格了,很舒畅的读完了。

《木 桶》
唯一能确定的是,她曾经装下了一条河流
水草,几条鱼,几场大风制造的漩涡
还有一条船,和那个妖女昼夜不息的歌声
中午,在河边捶衣服的时候
她不再看河水里的倒影。也不再猜想几千年前
河流上源那个腰肢纤细的女人
怎样把两个王朝装在她的左右口袋里
在这么热的中午,她如何让自己袖口生香呢
最初,她也以杨柳的风姿摇摆人生的河岸
被折,被制成桶,小小巧巧的,开始装风月
桃花,儿女情长,和一个带着酒意的承诺
儿女装进来,哭声装进来,药装进来
她的腰身渐渐粗了,漆一天天掉落
斑驳呈现
而生活,依然滴水不漏
她是唯一被生活选中的那一只桶
《横店村的下午》
恰巧阳光正好,照到坡上的屋脊,照到一排白杨
照到一方方小水塘,照到水塘边的水草
照到匍匐的蕨类植物。照到油菜,小麦
光阴不够平整,被那么多的植物分取
被一头牛分取,被水中央的鸭子分取
被一个个手势分取
同时,也被我分取
我用分取的光阴凑足了半辈子
母亲用这些零碎凑足了一头白发
只有万物欢腾
—它们又凑足了一个春天
我们在这样的春天里
不过是把横店村重新捂热一遍
《晚安,横店》
快四十年了,我没有离开过横店
横店尾部很轻的方言,如风线下沉
一个人就是一个下沉的过程,包括庄稼,野草,兔子
和经过村庄的云
沉到地上,渗进泥土,悄无声息的
我不能说爱这寂静,和低于一棵狗尾巴草的宿命
一棵桃树开花,凋零,结果
一片庄稼生长,开花,结果,收割
这些一年年轮回,让我有说不出的疼痛
越来越沉的哀伤
在这无法成眠的夜晚,风在屋檐盘旋
而我落在这里,如一盏灯关闭的瞬间
我口齿不清地对窗外的田野说一句:
晚安
我们同葬于泥土,距离恒定
——《关系》
我是一个没有来处水袖长飘的女人 老是老了 只有眼睛能窝住一湖水
——《烛光》3
不管厚土多厚,一个人走进去 总是很轻
——《后山黄昏》
如果十月安慰我,就允许五月烫伤我
——《2014》
一朵花有两个春天是不公平的
——《莫愁街道》
能够思念的人越来越少。我渐渐原谅了人世的凉薄 如果回到过去,我确定会把爱过的人再爱一遍 把疼痛过的再疼一遍
——《人到中年》
作为一个农人,我羞于用笔墨说出对一颗麦子的情怀 我只能把它放在嘴里 咀嚼从秋到夏的过程
——《五月·小麦》
你看,我不打算以容貌取悦你了 也没有需要被你怜悯的部分:我爱我身体里块块锈斑 胜过爱你
——《我想要的爱情》
刚开始读觉得这本诗集有些寡淡,后面越读越能感受到作者见微知著,与自然和谐的对话,余秀华可以在一株狗尾巴草上嗅出夏天,可以从风中感受到时光的流逝,心思细腻,目光敏锐,用纸笔写下无法说出口的感情。
碎碎念
前些天有个高中朋友,叫做A,来问我以后什么打算,聊着聊着开始叙旧,提到了一个老师,我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熟悉,就问他这个老师教我们的啥。他很惊讶地说,我们高二的数学老师啊,我和他喝酒,他忘了咱们班几乎所有人,但还记得你我和B。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小小的震撼,瞬间把我拉回了高中。这个数学老师是个特别负责任的人,不是班主任,但胜似班主任。我也非常适应他讲课的风格。我的成绩并不突出,性格也不是很活泼,我猜大概率是因为我和A同学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坤”(曾经很巧我和A同学一次物理小测考了一样的分数,我们的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念成绩的时候说“二坤”)。
这位数学老师是个比较雷厉风行,做事直率,为人实诚的人。他和A同学喝酒的时候,估计酒到酣处吧,说了很多话,受人排挤,职场不顺。我也算能理解原因吧,我的高中是私立高中,隶属于一个大的教育集团,大部分职位常年不换人,他对A同学说:“我不想巴结任何人”。
学校于我而言,像是只存在于回忆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单纯和美好。
做不完的卷子,追不到的女孩,看不够的夕阳,能够握在手里的命运。
我曾经看《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颇有感触,想效仿这个风格拍一部属于我自己的纪录片,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经历,记录属于我自己的回忆,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文字,拍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照片,有迸发的热情,也有无从下手的困惑。
假如毕了业再没有见面的机会,那在老师和同学的脑海与记忆中,我是否像已经逝去的人一样,人生就像谱上的休止符定格在了分别的年纪。
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死去。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在我的世界里已经死去。
但是在学校里,不存在时间的约束,高中校园永远是十七八九的年轻人,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将来也会是。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但门禁系统再没我的信息与数据,老师同学已将我遗忘,校园卡也消了磁,我也是另一副模样,保安以待陌生人的态度将我拒之门外。我真的在那里生活过吗。
分享几首最近一直在听的歌
New Order乐队的《Ceremony》单循了好久好久,原是Joy Division乐队的歌曲,主唱Ian去世后,其余成员组成了New Order乐队,并将其重新演绎。两个版本各有优劣,这里不讨论,两个乐队我都挺喜欢。
LINKIN PARK自CC去世后沉寂了好久,在专辑《Meteora》二十周年之际回归,并拿出了存货,同样单循了好久,能再听到CC的声音真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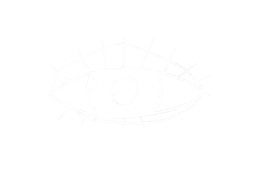
从十年之约来看看。青春一去不复返。很喜欢博主的主题风格,点个赞。
谢谢喜欢